我一直觉得,我和父亲前世肯定是仇人。上一世的恩仇未了,这一世来结。
父亲生于旧社会,长在战乱中,听他说起小时候的事,记忆最深的便是“跑老东”——躲避日本兵的追杀;其次便是对我爷爷的控诉。我父亲和我爷爷是一对冤家。父亲九岁时,我奶奶去世,据说爷爷扔下了父亲不管,自己去湖南华容县讨生活了。在我小的时候,每每不听话时,父亲就会板着脸吼我们,“老子九岁就自立了。”然后数落我们如何无用。父亲每数落一次,我在心里对他的不满就加深一层,以至于后来听到“九岁就自立”这句话就反感,无论他是以何种语气说起,也无论父亲是对谁说起。
父亲也曾说过,他一定是前世欠了我的,这一世还债来了。因此,在父亲和别人的交谈中,我被塑造成了“讨债鬼”。每次和父亲争吵之后,父亲总是痛心疾首地对我说:“养儿方知父母恩。”又说,“天下无不是之父母,只有不孝的儿女。”我像反感父亲说他九岁就自立一样反感这两句话。我觉得父亲这句话太霸道,不能因为你是父亲,你就永远是对的;我是儿子,就永远是错的。其实现在想来,我当时不单单反感父亲说这样的话,我对父亲的反感是全方位的,觉得父亲一无是处。
我和父亲曾经度过了短暂几年亲密时光,待我稍大一点,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父子之战。我很愿意回味和父亲有过的短暂的亲密时光,但那些记忆大多发生在我六岁之前,因此还留有模糊记忆的便很少了。我记得冬天的晚上,父亲教我唱“我是一个兵,癞子老百姓,革命战争考验了我,打倒解放军”。我一直不能理解这歌词,“癞子老百姓”倒好理解,那时农村的卫生条件极差,长癞子的人很多,我的妹妹就长了一头的癞子,但为什么要“打倒解放军”呢?多年以后我才知道,原来歌词是“我是一个兵,来自老百姓,革命战争考验了我,打倒蒋匪军”。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,还有一个亲密的记忆,是我五岁时,跟随父亲一起去镇上的剧院看了一场舞台剧《刘三姐》,结尾时,穆老爷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砸死了。我不能理解,每演一次戏,就要死一个人,那谁还愿意演穆老爷?父亲没有回答我,只是摸着我的头笑笑。父亲的这个动作,让我多少有点受宠若惊,也许是父亲极少用这样亲昵的动作表达他对孩子们的爱吧。这个摸头的动作,在我童年、少年的记忆中,就显得弥足珍贵,以至于多年以后,我依然记忆犹新。除此之外,我搜肠刮肚,实在找不出还有什么深切的,能体现父子间曾经有过亲密时光的佐证。而对于挨打的记忆,却是随手可以举出一箩筐。

父亲说:不打不成材。
父亲说:棍棒底下出孝子。
父亲说:三天不打,上房揭瓦。
父亲甚至有些绝望了:你狗日是属鼓的。
我不知道,少年的我有多么调皮,有多么讨人嫌。俗语云:七八九,嫌死狗。我就属于那种能嫌得死狗的孩子,而且不只局限在七八九岁。我把堂兄的头打破了,堂兄扬言:“么子亲戚亲戚,把亲戚拆破算了。”为此,我被父亲猛抽一顿,罚跪半天,不许吃饭;我不上学,偷偷去游泳,又被父亲狂扁一顿,外加罚跪到深夜;我在外面和同学打架,被打得头破血流,天黑了才敢回家,天没亮就溜去学校,直到头上的伤口长好,最终被父亲知道,还是补了一顿打;我和同学打架,以为神不知鬼不觉,结果同学的父亲打上门来,我再挨一顿揍;在我们兄妹中,我大抵是挨打最多的孩子。父亲打我时,我站着不动,任父亲打。任父亲打也罢了,我偏偏还嘴硬,说,“你打呀,反正我的命是你给的,打死我算了。”父亲说,“你以为老子不敢?打死儿子不犯法。”父亲举出了一堆父亲打死儿子大义灭亲的典故,那些不知哪朝哪代的传说,对我没有威慑力。我还记得,大年三十,孩子们都在撒欢玩耍,而我却被罚去野外拾满一筐粪才能回家吃团年饭,原因是我期末考试的成绩不理想。为了完成任务,我从别人家的粪坑里偷了一筐粪,没想到英明的父亲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把戏,说,老子晓得你不会老老实实去拾粪。自然,我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惩罚……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记住了这么多挨打的往事,而且记忆如此的深刻。如今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时,心里涌起的,全是幸福与温暖,这是我与父亲几十年父子情最为生动的细节。而在当时,每一次挨打,都在我的心里积累着反叛的力量。还没有能力反抗父亲,我所能做的,就是摆出一副不服气的架势,任凭父亲将竹条抽打在我的身上。跪在地上几个小时,我也不会服软认输。这让父亲更加恼火,对我的惩罚也更加严厉。父亲打骂我时,母亲是不能劝解的,若是劝解,父亲会连母亲也一起骂。父亲说,老子不信收拾不了这个油盐不进的枯豌豆。母亲能做的,就是偷偷拿一个枕头垫在我的膝下,让我跪着舒服一点。父与子的战争,从一开始,就是不对称打击。我只有挨打的份,而没有丝毫反击的能力。但是我在积蓄着力量,我梦想着早一天长大,长大了,就可以和父亲分庭抗礼了。

崔广志作品 春风
我还没有长大,庇护着我们兄妹的母亲就去世了。那一年,母亲38岁。我读小学五年级,小妹才八岁,哥哥和二姐都在读初中,因此,喂猪做家务,都压在了大姐的身上。父亲拉扯着我们五个孩子,那几年,家里显得清冷而凄惶。父亲变得温和了一些,一家人在一起时,有了点相依为命的感觉。母亲的去世,也让我们兄妹五个仿佛一夜间长大了。大姐是没有上学读过书的,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很快,二姐初中毕业后,也回家务农了。接着哥哥也不上学了。那时,我经常能听到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,在经过我们家门口时发出的赞叹——
说:这就是昔文的几个伢们,没有姆妈,伢们一个个还穿得干干净净;
说:你看他们家门前收拾得那个干净;
说:看那菜园子,菜长得极喜人,没妈的孩子早当家;
说:唉,又当爹又当妈,不容易!
每当听到这样的话,我的心里就会发酸,会有一种莫名的屈辱感。读初中后,我渐渐能体会到父亲的艰辛,觉得父亲是真的了不起,我也在心底里发下誓愿:要带着我这个贫穷的家庭走向富裕。但这并不代表我和父亲的关系开始走向和解。比如,邻居们当着父亲的面夸奖我们姐弟。
说:你的这几个伢们个个懂事。
父亲说:懂屁事,没一个成器的。
说:我看世孝将来能上大学。
父亲说:上农业大学,摸牛屁股的命。
说:世孝长得好,将来不愁说媳妇子。
父亲说:鬼才看得中他,打光棍的命。
说:你不愁啊,再过几年,伢们大了,你就退休享福了。
父亲说:老了不像《墙头记》里的那样对我就阿弥陀佛了。
那时正在放电影《墙头记》,讲两个不孝儿子的故事。
父亲把他对儿女的贬损看成是谦虚,但我听了很是不满。我觉得父亲把我们和《墙头记》里的不孝儿子相比,是对我的侮辱。我觉得父亲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孩子,为此我甚是讨厌父亲那所谓的谦虚。有一次,当父亲再次在别人面前谦虚时,我终于忍受不了,大声地吼叫了起来。父亲那次倒没生气,只是说,“你要真有出息,那就是我们老王家祖坟冒青烟了。”我说,“你等着瞧。”父亲说,“我还看不到?你能出息到哪里去?”现在我知道了,父亲当时心里其实并不这样想,父亲也认为他的孩子们是懂事的,也认为他的孩子们将来会有出息,但嘴上偏偏不这样说。多年以后,我和父亲小心地谈到这个问题,父亲说,请将不如激将。原来父亲是在以他的方式激励我们。从记事起,到现在,我快40岁了,还从没有听父亲夸奖过我,鼓励过我一次。父亲不知道,在欣赏中长大的孩子和在贬损中成长的孩子,内心深处有着多么大的不同。

曾庆全作品 家肥屋润
父亲本来话就不多,母亲去世后,父亲更加沉默寡言。他的心里装着五个孩子的未来。他有操不完的心,为了我们这个家。但父亲从来不与我们沟通,不会告诉我们他的想法。我和父亲总是说不到一块儿,我们兄妹几个,都和父亲说不到一块儿。吃饭时,父亲坐在桌子前,我们兄妹就端着饭碗蹲在门外吃,父亲吃完下桌子了,我们呼啦一下都围坐在桌前。有时我们兄妹有说有笑,父亲一来,大家就都不说话了,我们兄妹无意中结成了一个同盟,用这种方式孤立着父亲,对抗着父亲。时至今日,我也无法想象,当父亲被自己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们孤立时,心里是什么感受。后来我出门打工,也为人父了。真的如父亲所说,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,我开始忏悔了。回到家里,吃饭时,我会和父亲坐在一起,我吃完了,也会继续坐着等父亲吃完饭。虽说有那么一点别扭,有那么一点不习惯。但我开始懂得了反思,也试图去理解父亲,父亲是爱他的孩子们的,只是父亲不懂得怎样去表达对孩子们的爱。
父亲是希望能在他的儿女中出一个大学生的。这希望首先寄托在我哥哥身上。我哥哥读书很用功,学习成绩也很好,但不知为何,平时成绩很好的哥哥,中考却考得一塌糊涂,以至于老师都深感惋惜。父亲希望哥哥复读,老师也希望哥哥复读,但我哥哥死活不肯读书了。那时我妹妹读完小学四年级,也不肯读了,于是父亲的希望便寄托在了我的身上。小学升初中,全乡五所小学,我考总分第一。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,没有夸我,但我知道,父亲对我寄予了厚望,希望我将来能上大学跳出农门。
然而我终于让父亲失望了,上了初中,我的代数、几何、英语出奇地差。这几门功课考试从来没有超过50分。初中毕业,我回家务农。父亲劝我去复读,父亲说,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”我实在对上学没了兴趣,也作好了被父亲狠揍一顿的准备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这次父亲没有打我,也没有骂我,劝我无果之后,也尊重了我的选择。相反,较长的一段时间,父亲对我说话都有一些小心翼翼,甚至低声下气。父亲以为我一定为没有考上高中而伤心欲绝,父亲不忍在我的伤口上撒盐。我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。
这年,收完秋庄稼,农村就闲了。其时打工潮还没有兴起,乡村里许多像我一样辍学的孩子,一到冬天就成了游手好闲的混混。第二年春天,父亲相信我心灵的伤口已经痊愈,说,“从今年开始,要给你上紧箍了,这么好的条件供你读书你不争气,也怪不得我这做老的了。从今年起,你老老实实在家里跟我学种田。”于是这一年,我像个实习生一样,跟着父亲学习农事。清明泡种,谷雨下秧,耕田耙地,栽秧除草,治虫斫谷,夏收秋种……从春到秋,几乎没有一天闲。忙完水田忙旱地,收完水稻摘棉花。好不容易忙完这些,又要挑粪侍弄菜园。冬天到了还要积肥。沉重的体力活,压在了我的肩头,那年,我16岁。父亲对我说,“要你读书你不读,受不了这份苦吧,受不了明年去复读。”而我想到读书要学英语,还有那让人脑袋发麻的代数、几何,就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。父亲于是开始叹息,说他那时是如何的会读书。我反驳,说那时只读“三百千”,我要搁过去,也能考个秀才举人,说不定还能中个进士呢。因为整个初中时期,唯一能引以为豪的是我的语文成绩,作文总是被当作范文贴在墙上。父亲说,那我还会打算盘,你可会?我哑口无言。
遵祖宗二家格言,曰勤曰俭;教子孙两行正路,唯读唯耕。父亲恪守着这样的古训,认为既然他的儿子成不了读书人,那就当个好农民吧。父亲常说,你连耕田都学不会,将来我死了,你的田怎么种哟?我不满意父亲的唠叨,说车到山前必有路。那时我16岁,个子比父亲还高了。和父亲说话,像吃了枪药,常常是父亲一句话还没说完,便被我呛了回去。父亲就不再说话,发一会儿呆,然后长叹一声。我和父亲的战争态势,随着我的成长,渐渐发生了变化。由过去的力量悬殊的不对等打击,变得渐渐有点旗鼓相当。父亲还是骂我,但我总是还以颜色,表现出我的反感与不满。那时我迷上了武侠小说,只要有一点空闲,就捧起小说看。这也是父亲无法忍受的。父亲说,让你读书你不读,现在回家种田了你又读得这么起劲,根本就是想偷懒。父亲在多次教训我无果后,也只好长太息而听之任之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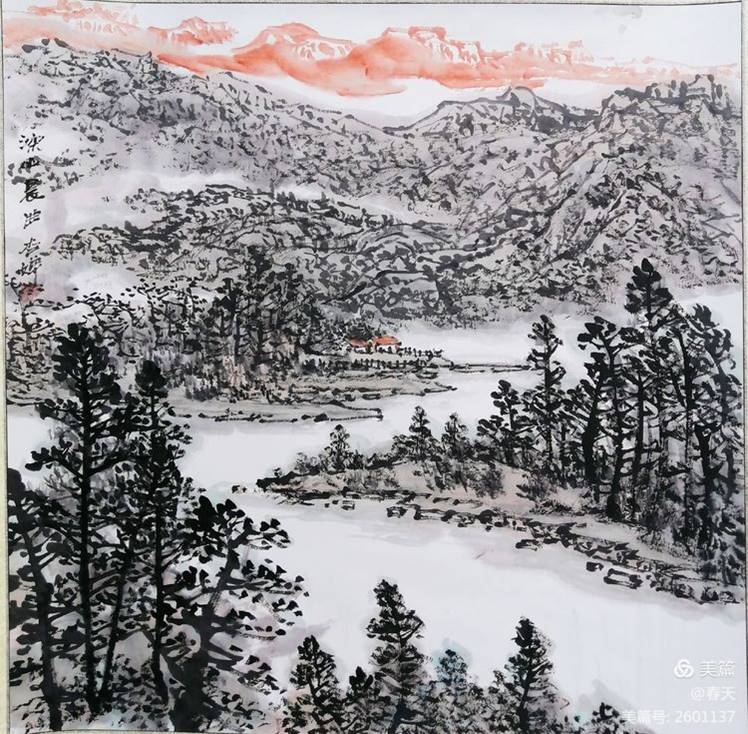
韩杏婵作品 深山晨曲
在几个孩子的婚事上,父亲再一次显示出了他的专制。大姐的婚事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自然是较让父亲省心的。我二姐和小妹,年轻时都是村里数得着的美女,追求者众。父亲说,男怕入错行,女怕嫁错郎。父亲觉得他有责任帮女儿把好这一关。
二姐的婚事,一开始就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。父亲并不是反对后来成为我二姐夫的那位青年木匠,青年木匠手艺不错,人也还本分。父亲不满意的是青年木匠的家庭,自然也不是嫌贫爱富,青年木匠的家庭还算富裕,比我家强得多。父亲不满意的是青年木匠家的家风,觉得那一家人有点虚浮,做事不踏实。没想到一贯文静内向的二姐,用激烈的方式表达着她对父亲的不满。二姐把自己关在家里哭了半天之后,选择了自杀。幸亏当时家里没有农药,二姐喝下了大量的煤油。二姐的自杀,对父亲的打击和震惊是巨大的。之后,父亲不再反对二姐的婚事,也不敢再用过重的言语苛责我的二姐了。父女的关系,也陷入了一种紧张的、小心翼翼的状态。
二姐出嫁那天,临出门时,给父亲下了一个长跪。二姐哭了,父亲也哭了。我跑到山顶,看着接我二姐的车远去,泪如雨下。我以为二姐是怀着对父亲的恨离开这个家的,我以为二姐用一跪斩断了父女20多年的感情。但是我错了,二姐出嫁之后,父亲对二姐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,二姐对父亲的态度也同样发生了极大转变。我想,二姐出嫁之后,父亲和二姐一定都在许多的夜晚思念过对方,二姐会想起父亲的养育之恩,想起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艰辛。二姐有了自己的孩子,正如父亲常说的那样,养儿方知父母恩。父亲呢,我只知道,许多的夜晚,他和衣躺在床上,很久,很久,然后用一声沉重的叹息结束一天。父亲一定是后悔了,后悔没有给这个早熟、懂事、坚韧、勤劳的女儿多一些理解,少一些言语上的伤害。现在,二姐出嫁20多年了,她的孩子都已成人外出打工。我也目睹了这20年二姐所过的日子。我不知道我的二姐是否幸福,最起码,从我的角度看,我觉得二姐不幸福。那个青年木匠,我的二姐夫,没能好好呵护疼爱我的二姐。这一切,父亲都看在眼里,但父亲再没有对二姐和二姐夫的生活多说一句什么。父亲说,那是她自己的选择。
命运总是惊人地相似,同样的事情,在小妹的身上居然重演了一次。当年一头癞子的小妹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时,一位青年教师走进了小妹的生活。青年教师聪明,帅气,读过我们县最好的高中,能言善辩,才华出众。从某些方面来说,他和小妹是很般配的一对。但他们的爱情,同样遭到了我父亲的强烈反对。父亲甚至不许那个青年教师到我家里来。父亲反对的理由很简单,他觉得青年教师的父亲不成器。父亲深信那句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的老话,并反复用这句话提醒我妹妹。然而小妹深爱着那位青年教师。小妹的性格和二姐相反,二姐外柔内刚,小妹却是个烈性子。她不会像二姐那样选择用死来对抗,而是坚定地和青年教师交往,非他不嫁。我坚定地站在小妹这一边。青年教师来我家,父亲不理他,而我却热情地接待他。二比一,我和小妹终于战胜了父亲。父亲说,你们都大了,你这当哥哥的作了主,我也不说什么了,只是你们将来别后悔。
小妹出嫁时,我在南海打工,没能回家。那天,故乡下大雪。南海也很冷。我想到那天我的妹妹出嫁,从此她的生命中,将有另一个男人用心爱她,照顾她,感到很欣慰。也有一些伤心,一个人躲在宿舍里默默流泪。妹妹出嫁后,父亲接受了这一现实,他对小女婿一样地疼爱,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,仿佛过去的对立统统不曾存在过。妹妹和二姐一样,出嫁后仿佛变了个人,和父亲开始有说有笑,回到家,吃饭自然是坐在一桌。后来小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,她和青年教师一起在外面打工,东莞,中山,深圳。青年教师迷上了赌博,还在澳门的赌场赌过,欠了“大耳窿”的高利贷,弄得我妹妹也被“大耳窿”追杀,连夜仓皇从中山逃到深圳,投奔我这不成器的哥哥。青年教师说他没办法改掉这些毛病,自认没救了。妹妹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离婚时,妹妹坚持要孩子。我说,不管你选择什么,我都支持你。那一刻,我想到了父亲。我想,也许当年我错了,父亲是对的。父亲以他几十年的人生阅历,能透过人的表象看到本质。也许,我们谁都没有对,谁都没有错。但我知道,此时此刻,还有一个人心里和我一样难受,甚至比我要难受得多,那就是我已年迈的父亲。

黄春梅作品 乡情秋意浓
多年的父子成仇人。如果不是我出门打工,和父亲有了空间上的距离,我和父亲的战争,也许还会升级,更不会像现在这样得到化解。我和父亲关系最为紧张的是1987年到1992年,那段时间,我们对于任何事情的看法都有分歧。记得有一次,荆州地委行署要来我们村检查计划生育,村里下了通知,谁也不许乱说话,如果乱说,家里有学生的要开除,种地的,要把地没收,总之是下达了封口令。这个封口令让血气方刚的我和我的几位同党深感不满。我们叫嚣着,说每个孩子都有上学的权利,谁也无权开除,并扬言要去告状,要揭发我们村的黑幕。地委检查组的人来的那天,我们一行人守在村部,作好了“告御状”的准备。也是不凑巧,地委的人在来我们村的路上,接到通知,说是邻村因计生工作不当,出了人命,于是他们直奔邻村而去。事后,村里的领导开始秋后算账,几位干部来到我家质问我,我当然是跳起来和他们对着干,并扬言,他们要是敢整我,我就把村里的事曝光到报社。干部说,好,你狠!将来总有一天你会落到我们手上。我说你放心吧,不到法定年龄我不结婚。干部说,你敢保证你头胎就生儿子。我说生儿生女都一样,我只生一个。干部认为我说大话,虽说不至于没收我家的土地,但对我甚为不满,本打算来教训我一下,出一口气以儆效尤,谁知碰上我这样的“二百五”。父亲深为我感到担心,怕我将来在村里没法混,被干部穿小鞋,便大声喝斥,教训我,让我认错。我的叫声比父亲的声音还要大,我觉得我是正确的。父亲气极,随手抓起一把椅子砸向我,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样,站在那里不动,说,砸啊,你砸死我,我也没有错。村干部并没有去夺我父亲手中的椅子,父亲手中举起的椅子终于是向我砸下,正砸中我的肩膀。肩上的痛是次要的,我觉得这一椅子,砸碎了本来就脆弱不堪的父子之情。我离家出走了,而且一走就是一个多月,我跑到县城一位开餐馆的同学家,同学家做鱼糕鱼丸卖,我给他们当帮工,杀鱼,打鱼糕。眼看要过年了,父亲让小妹来县城找我,我才回家过年。
那时我觉得我们家庭的贫穷,是因为父亲不会持家造成的。父亲只会死种地,而我却总是想着搞一些新的实验。并在深思熟虑之后,向父亲的权威提出了直接的挑战,说,从明年开始,我来当这个家。父亲冷笑,告诉了我家庭的财政赤字是多少,我吓得打了退堂鼓。
出门打工后,我和我出嫁的姐姐们一样,开始觉出了父亲的好,觉出了父亲的不容易。我给在家里的妹妹写信,总是要问父亲好不好。妹妹给我回信,也会报上家里的平安。我们的信,都是报喜不报忧,而报喜时,也是把喜夸大了许多。父亲觉得儿子终于是出息了,我回到家里时,父子间,有了难得的亲密。记得有一次,打工多年的我回到家中,家里已没有了我的床铺。晚上,我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。我觉得很陌生,很别扭,也很温暖。我想父亲也多少觉出了一些不自在。父子俩都不说话,我不敢动一下,父亲也不敢动。我佯装睡着,很晚,很晚。父亲粗糙的手,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我的脚上,见我没有反应,父亲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脚。温暖在那一瞬间把我淹没,我觉得我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,是那个童年时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,跟着父亲学唱“我是一个兵,癞子老百姓”的孩子。我不敢动一下,享受着来自父亲的关爱与温暖。我的泪水,打湿了枕头。我的脚终于动了一下,父亲的手像触电一样,弹了回去。我渴望着父亲再次抚摸我的脚,但父亲没有。良久,父亲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。我突然发觉,我不再讨厌父亲的叹息声,在外面流浪多年,历经冷暖后,我终于读懂了父亲沉重叹息里的爱与无奈。
我以为,我和父亲,再也不会发生冲突了。我以为我长大了,再也不会惹父亲心烦。但儿子终究是儿子,在外面受人冷眼,受人打击时,我也学会了隐忍。可是在父亲面前,我永远也学不会,我还是我,我不想压抑自己的情感。而父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真正转折点,是在我结婚之后。婚后,打工多年的我回到了家,做起了养殖发家的梦。我养了许多猪,为了这些猪,我再次和父亲发生了冲突。自从我结婚后,父亲心甘情愿地退居二线,什么事都不再作主,由着我来。两次争执,和从前也有了很大的转变。一次是我想把菜园全部种上猪菜,父亲却一定要在大片猪菜中辟出一小片来种辣椒。父亲把我种好的猪菜锄掉,说他要种辣椒。在我们那里,没有辣椒,简直是没办法吃饭的。但我反对父亲在那块地里种辣椒,我说可以去另一块菜地种。父亲坚持,说他就要在这里种,似乎没有什么理由。父亲买来了辣椒苗,自顾自地栽他的辣椒苗。我生气了,说,你栽了也是白栽,今天栽,我明天就给你挖掉。父亲挥动着锄头,说,你要是敢挖掉,老子就一锄头挖死你。我突然觉得,父亲还是从前的父亲,儿子也还是从前的儿子。不过父亲在说完这句话后,突然变得很伤感,不再言语,默默地栽完了他的辣椒苗,回到家中,发呆。我也并没有挖掉父亲的辣椒苗,但这件事,还是伤了父亲的心。还有一次,栏里的猪开始转入育肥期,这时要让猪多睡,由过去的一日三顿改为一日两顿,猪们开始不习惯,在栏里叫得凶。父亲看着猪们可怜,自作主张拿了青菜去喂,我觉得父亲不该干涉我科学养猪,于是把父亲数落了一顿。父亲很委屈,一言不发,回到房间就睡了,也不吃饭。父亲用绝食对抗着来自儿子的暴力。我投降了,彻底服输,第一次自动地给父亲跪下,我说,你不吃饭,我就不起来。
父亲老了。老小老小,父亲变得像个孩子。
父亲再不骂人了,再不打人了。父亲变得平和了,慈祥了。

陈阜东作品 回归自然
但我们兄妹一个都不在他身边。我们常年在外,也难得顾上父亲,除了给父亲寄生活费,实在没尽过什么孝道。父亲说他其实不需要钱,父亲需要的,我们却不能给他。父亲需要我们在身边,哪怕烦他,让他生气,也比看不到我们,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强。好在,那些年,大姐一直在家,每月回家帮父亲洗一次被子。父亲的生日,端午,中秋,她都会回家看看。这是父亲唯一能享的亲情。2004年,我的大姐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。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。父亲说,人生最大的不幸,少年丧母,中年丧妻,老年丧女,都被他遇上了。
次年春节,我把父亲接到深圳过年。父亲第一次来深圳,我的女儿子零天天陪着爷爷到处转。父亲像个孩子一样,陪孙女去公园钓金鱼,花了几十块钱钓到三条金鱼,又花钱买了一个鱼缸,和孙女兴冲冲地回到家里。那时我失去了工作,在家自由撰稿,文学刊物还没有开始接纳我的小说,发表极困难,差不多是在吃老本,经济状况极差,父亲却花了近百元,只是为了逗孩子开心。我再次数落了父亲。不过这次父亲没有生气,只是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,也不辩解。我一走,他就和孙女一起喂金鱼吃食,爷孙俩笑得很开心。
过年时,一家人围在电脑前看中央电视台为我录制的纪录片。看着看着,父亲突然痛哭失声,说,没想到,这些年你在外,吃了这么多的苦。不过很快又笑了起来。父亲说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事,说起我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淘气,没想到父亲记得那么多我儿时生活中的细节。有好多,我都没有一点印象了。在父亲的讲述中,我过去那些嫌死狗的往事,都成了今天能成为一个作家的异秉。父亲说,你从小就与别的孩子不一样,我知道你会有出息的。
37年来,我第一次听见父亲夸我。
过完年,父亲说,我要回家了。父亲不习惯住在这里,瘦了好几斤,三天两头打针吃药,父亲说他怕死在我家里,以后我女儿会害怕。送父亲上车时,我说明年过年再来吧。父亲很伤感,哭了。然而父亲一回到家,身体就好了,人又精神了。故土难离,父亲与那片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,已经是一个整体。而我,却成为故乡的逆子,再也回不去故乡。父亲回去后,我想,从今年起,没事多给父亲打打电话。但一忙起来,就把打电话的事忘了。父亲就把电话打过来,问我好不好,父亲说,没有什么比看到孩子都好,更能让他开心的事了。父亲说,你活一百岁,在我眼里,也是个伢。
写作这篇文章期间,我连襟打来电话,诉说他的儿子不懂事,快把他气死了,希望我能劝劝。我笑笑。没两天,又接到我姐夫打来的电话,劈头一句就是,“他舅舅,你帮我说说云云,这孩子,真是要气死我了。”云云是我二姐的儿子。接下来,我姐夫就历数了他儿子的种种异端。我笑笑,劝姐夫,孩子大了,要放手,让他们去按自己的方式成长。父与子的战争,在天下众多的父子间上演着,这是人生的悲剧还是喜剧?但现在,今天,当我回忆起与父亲在一起的往事时,所有的战争,所有的冲突,都成为我成长中最动人的细节,成为我与父亲今生为父子的最朴素的见证。这就是人生,许多的未知,要到多年之后回首往事时,才能觉出其中的奇妙。
多年的父子成仇人,多年的仇人成兄弟。诚哉,斯言。写下这些,献给天下的父与子。
作者简介:
王十月,本名王世孝。1972年生于湖北石首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,鲁迅文学奖获得者,两次入选“中国散文学会年度散文排行榜”。



